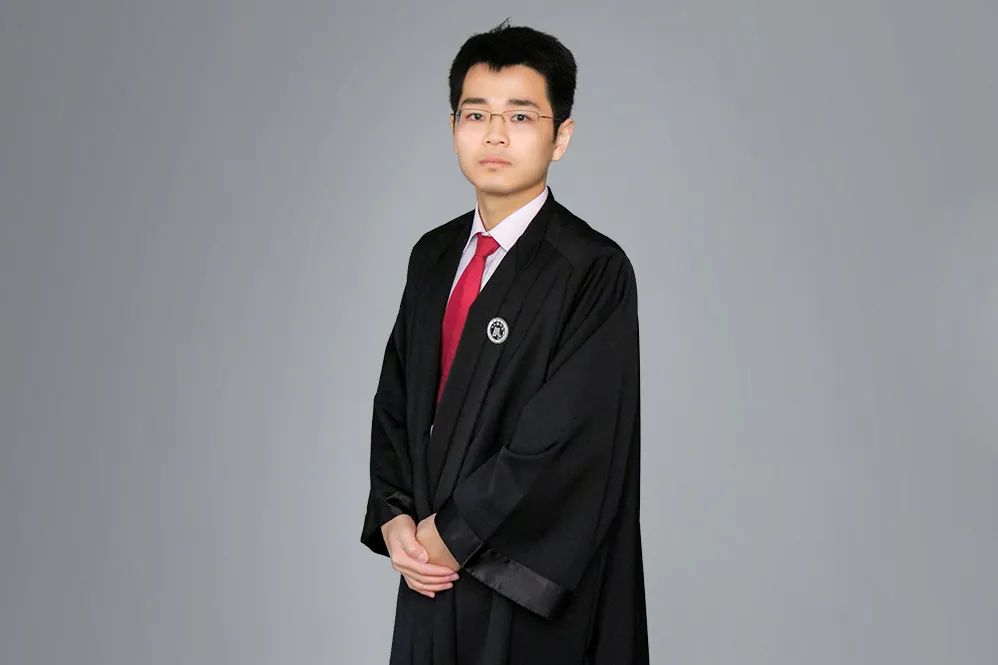
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 李明世
一、法律规定
刑法 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二、司法解释及指导文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公通字〔2010〕23号,20100507)
第七十七条〔合同诈骗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
第一条: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1〕21号)
1.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合同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根据诈骗手段、犯罪数额、损失数额、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
4.构成合同诈骗罪的,综合考虑诈骗手段、犯罪数额、危害后果、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
1、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数额较大”起点五千元的,在三个月拘役至九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诈骗数额每增加三千五百元,增加一个月刑期。
2.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诈骗公私财物,犯罪数额达到“数额巨大”起点十万元的,在三年六个月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诈骗公私财物,犯罪数额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五十万元,在十年六个月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三、要点解释
合同的理解
首先,刑法对本罪只规定了“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示限于书面合同,口头合同亦属于该范畴;
其次,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体现财产转移或者交易关系,为行为人带来财产利益的合同。第一,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主要是经济合同,诸如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合同,应当排除在外。第二,签订合同的主体可以是自然人或者单位。实践中相当多的经济实体往往以个人名义签订合同,如果将以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一概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之外,不符合平等保护市场主体的原则;
再次,“合同”除了要求具备经济实质之外,还应当体现“合同”的利用价值。换言之,“合同”在本罪中应当作为一个构成要件要素,必须体现“利用性”,这也是对刑法第224条作出当然解释的结论。即便合同本身具有经济性,但是犯罪的既遂与合同根本毫无关联的话,那么也不能简单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骗取对方财物中“财物”的理解
“财物”应当限定解释为“合同标的物”,如货款、预付款、担保财产或者定金等,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为了体现合同的经济实质。利用合同非法取得的财务如果与“合同标的物”无关,也不能认定为本罪。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
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应当注意两点:一是不能简单以有无合同为标准来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二是不能简单以“签订合同+骗取财物”为标准来判断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的本质是被害人基于合同陷入错误认识而交付财物,对于只是利用合同形式,但被害人之所以陷入错误认识并非主要基于合同的签订、履行,而是合同以外的因素使其陷入错误认识而交付财物的,应认定为诈骗罪。
所谓“利用合同”,是指通过合同的虚假签订、履行使得相对方陷入错误认识,从而交付财物,实现其非法占有目的。换言之,该合同的签订、履行行为是导致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而作出财产处理的主要原因。利用合同即是其诈骗行为的关键。
四、案例分析
严格区分合同诈骗与民事违约行为的界限。注意审查涉案企业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是否有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注重从合同项目真实性、标的物用途、有无实际履约行为、是否有逃匿和转移资产的行为、资金去向、违约原因等方面,综合认定是否具有诈骗的故意,避免片面关注行为结果而忽略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于签订合同时具有部分履约能力,其后完善履约能力并积极履约的,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温某某合同诈骗立案监督案,JZD91-2020〕
行为人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的一些行为具有一定欺骗性,但其主观上不具有以欺骗手段非法占有对方公司财产的目的,客观上具备一定履约能力,也有积极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动,拒退保证金是事出有因,并不是企图骗取对方公司的财产,不属于“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采取欺骗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隐匿合同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的情形,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吴联大合同诈骗案,GB2003-1〕
行为人通过签订“兼并”协议控制被兼并企业财产后恶意处分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关键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的认定:一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兼并合同过程中是否采取了欺骗手段,二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实践中,行为人不仅没有履行兼并合同的能力,而且在以零价格实施“兼并”后,并未按照兼并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而是恶意处分被兼并企业财产,其行为充分证明其主观上无任何履行兼并协议规定义务的诚意,应当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被“兼并”企业财产的主观故意,并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参考案例第211号:程庆合同诈骗案〕
行为人假冒国家工作人员,伪造工程批文,假借承揽项目需要活动经费的名义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都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实施的,即在与被害人签订所谓施工承包合同之前,其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被害人的财物已经被被告人非法占有,其虚构事实骗取钱财的犯罪目的已经实现。此外,行为人骗取钱财的行为并没有伴随合同的签订、履行,其非法侵占的财物亦不是合同的标的物或其他与合同相关的财物。虽然行为人事后也与他人签订了一个虚假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但这仅仅是掩盖其诈骗行为的手段,而不是签订、履行合同的附随结果,是否签订合同已经并不能影响其骗取财物行为的完成。可以看出,行为人虚构身份,以许诺给他人介绍承包虚假的工程项目为诱饵,借承揽工程需要各种费用为名目,利用他人想承揽有关工程项目的心理,骗取各被害人钱财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特征,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参考案例第403号:王贺军合同诈骗案〕
行为人与他人签订“聘请顾问协议书”,以自己承包的公司及自己成立的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揽出国签证咨询业务,收取他人钱款,许诺如办不成出国签证,再如数退还钱款。行为人所签订的“聘请顾问协议书”,表面上像一个咨询性质的协议,具有技术服务性质,但根据其提供的所谓服务内容,实质上是一个代办出国签证性质的委托代理合同。这种委托代理合同,具有一定的代理服务内容并体现了一定市场经济活动性质,利用这种合同实施的诈骗犯罪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代办出国签证的市场秩序,因此应认定为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合同。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之中,骗取的钱款正是合同约定的报酬标的,在没有为他人办成出国签证的情况下,携款潜逃,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应构成合同诈骗罪。
——〔参考案例第457号:宗爽合同诈骗案〕
职务是一项由单位分配给行为人从事的一种持续的、反复进行的工作,担当职务应当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而非单位临时一次性地委托行为人从事某项事务。行为人并不是公司聘用的职工,而仅系公司临时一次性授权的、只负责某项业务洽谈的代理人,故其身份不符合职务侵占犯罪、挪用资金犯罪所要求的主体身份,不能认定其犯罪行为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实施。行为人行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其与公司的协议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参考案例第716号:杨永承合同诈骗案〕
承运合同是市场经济中较为常见的一类合同,行为人事先签订合同,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将承运的优质豆粕暗中调换为劣质豆粕,事后又按合同约定运送至约定地点,其正是利用合同实施了诈骗活动,不但侵害了他人财物的所有权,而且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行为人系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合同实施诈骗犯罪活动,因此应当按照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参考案例第807号:张海岩等合同诈骗案〕
在合同诈骗案中,应当综合合同签订的背景、被告人为生产经营所作出的努力、钱款的去向和用途等方面来判断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不能简单地因被告人有欺骗行为直接得出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尤其是项目真实存在,行为人资产负债问题并不突出,合同相对方可以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在一定程度上可挽回损失的,不宜轻易认定为诈骗犯罪,这也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参考案例第1299号:高淑华、孙里海合同诈骗案〕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雷石普法 丨 企业家常见五大罪名解读(三)——合同诈骗罪